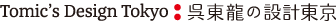|
Inside Out - 從建築延伸的無限想像
如同利用「空氣」包裝物品的「空気の器」,TORAFU ARCHITECTS反轉日常觀看的方式,打破建築、產品、室內設計的界線。就像他們強調的「Inside Out」-「表」與「裡」並不對立,只要掌握對映的特質,便能延伸無限想像。
TORAFU ARCHITECTS以知弘喜愛的「帽子」造型,設計出讓孩子能夠自在玩耍的「Children’s Room」。這次誠品R79的創作展中,這頂「帽子」也將跨海來台展出,其共同創辦人鈴野浩一將與台灣觀眾分享此次創作過程,藉由過去作品與觀眾分享設計的樂趣,並重新思考其本質。 - Q. 鈴野先生有兩個女兒,也參與了知弘美術館裝置設計,怎麼樣培養小孩子的美感,對鈴野先生來說? A:我有兩個女兒,他們的個性都非常不一樣,教育的問題我比較想請教別人。 Q.會在意他們比方說生活美感的選擇,或是教育,或者是家裡空間上的一些設計? A:鈴野先生的太太是澳洲人,小朋友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文化當中,鈴野先生也想的非常多,認為澳洲跟日本的文化看似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實是非常的不一樣,每一次去澳洲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因為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回頭來看自己日本的文化到底是怎麼樣,接受一些不一樣的刺激。 Q. Torafu這個名字在2004年是怎麼誕生的?他有沒有特別的意涵,他的背景是什麼? A:我講了你可能會失望,這名字一點意義都沒有,就是覺得聲音,用聲音來決定。我們剛開始是做建築的!建築設計事務所,日文寫起來也是這幾個漢字,一模一樣的,看起來硬梆梆的,我想讓他稍微軟化一下,所以前面Torafu,在日文是寫成一個片假名,包括聲音、字型上面看起來稍微有感情。 Q.剛剛已經看過非常多不同的案例,對於事務所來講,有很小的,也有大到房子,對於他們在接案子或是做設計的時候,會怎麼去選擇他的優先順序,大小嗎?還是其它原因? A:首先,我們並沒有用案子的大小來決定要不要接這個案子,以前曾經有一個攝影師跟我講過,一件事情要做到好,就像是打棒球揮棒的打擊,至少要練習一千次,一樣的道理,做任何工作,都要從訓練開始累積,剛開始我們創業初期也沒有選工作,只要有願意就配合,我們就接了,到現在比較多的趨勢是以前做過專案的延伸,或者做過一些案子有相關的關係來委託我們的比較多,像我們第一個作品,就是飯店的那個作品,以一個案子的條件來講,其實並不是太好,因為東西非常地亂,預算也不多,如果今天我們是用預算的規模或是案子的大小關聯來選的話,我們一定不會選擇到他,但是有時候我也會想說,一個東西就是因為他的條件那麼的不好,所以我必須去發揮我們的想像力,發揮我們的創意去讓它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也因此可能會在那個衝突的狀況下可能想不太到的點子,所以我覺得我們向來不用大小來決定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Q.我看到很多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案子,比方說蓋一個房子的know-how或者是在做一個紙的製品的延伸,其實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當做到不同類型的領域,可能很多知識,或者是需要琢磨、需要學習的部分要從頭來過,對於這麼多樣類型的案子,這個部分在接案的時候是不是很困難?或是很麻煩的事情呢? A: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做很多不同領域的東西,所以每次面臨一個新的案子的時候,我反而比較容易、比較快去發現這個案子最重要最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Q.從做一個案子來講,今天看到很多棒的作品,從一開始的發想到最後作品的生成,這個中間的變化會很大嗎?就是包括想法或是素材的使用,或者是結構造型這些?一開始的想法會不會變化非常大? A:其實我們在做東西的時候,我常會覺得說光是靠我一個人想出來的東西沒什麼意思,所以我喜歡跟我公司的同事,或者甚至是跟我的業主一起發想,在這個思考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很多本來就沒有預期到的東西,像是做一個模型,可能這個模型真的做出來以後,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是你想不到的,而這些出乎意料東西本來就是理所當然會發生的。 Q.講到分工的話,你們是怎麼樣去進行分工? A:我和我另外一個合夥人,我們的分工方式並不是說,這個案子你的,這案子我的,因為如果都分開做的話,這樣合夥就沒什麼意義了,我們的分工方式有點像是我來做整體的規劃、概念,等於是一個大方向,接下來要去落實的部分,執行上就會由禿真哉先生做比較細部的規劃,從我們剛剛介紹第一個飯店內裝的案子就是以這樣一個分工的方式進行。 Q.未來有沒有可能來台灣承接一些案子或是做展覽? A:希望有一天可以受到邀請,我很喜歡台灣。 Q.很遺憾因為我沒有去過知弘美術館,不管是東京或是長野,是否可以用一個建築師,設計所的身份來推薦、或是形容美術館哪個地方特別迷人,或是建議我一定要去感受它魅力的地方? A:其實我一直都久聞岩崎知弘老師的大名,知道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內藤廣先生幫安曇野美術館打造這樣一個建築,我也是曾看過他的作品,但我也是希望我能夠去,但很遺憾我也是直到目前為止也是還沒能夠去。 知弘美術館有兩座,一個是在東京、一個是在長野,而我這次擺放我的帽子的作品就是在安曇野這個地方,以一個建築師團隊才會看得到注意到的地方來建議,在那時候因為我們要佈展,所以我就在那個館內待上很長的一段時間,一整天都待在那邊,所以可以發現這個地方從早到晚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表情,也很想再待久一點;另外還有一點是這個美術館非常不拘小節,你要釘釘子沒有關係,地板磨了一點點也沒有關係,他們會認為這些東西留在美術館的東西就當作是一個痕跡,一個歷史得去接納它,這樣一個不拘小節的心態也是我很喜歡這個美術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