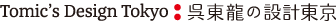|
回到美好年代的TOKYO 1964
東京是全球唯一舉辦2次奧運的亞洲城市,當大家歡欣期待2020東奧來臨,在半世紀前的1964年奧運,更令全日本引領期盼,較今日絕有過之而無不及!原來時代環境與種種氛圍促使了這股強大的能量,而我趕在東京奧運倒數一年前在東京墨田〈江戶東京博物館〉看了檔名為「江戶運動與東京奧林匹克」特展,彷彿搭乘時光機來到第18屆東京奧運,發現美好年代裡的種種榮光及其劃時代意義。
〈江戶東京博物館〉是紀錄德川家康進入江戶後約400年間迄今,從「江戶」經明治維新成為「東京」的歷史軌跡。建築由代謝派建築大師菊竹清訓以四柱二樑的特殊架高結構為其設計特色。外觀被戲稱為大木屐,偌大的內部展區則分「江戶」與「東京」。而這個展覽結合館藏的「江戶」資源加上「東京」奧運史料,編集出繼往開來、相互呼應的展覽特色。 早在江戶時代就十分風行體育,例如:相撲、蹴踘等,且不僅侷限於貴族階層,家境富裕的社會階級也相當重視體育,各有專門的著裝配件毫不馬虎。當時的武士素養有馬術、弓術、劍術、水術等在藩校都有教導,卻因實無戰事而顯無用武之地。 到了近代,日本結束鎖國接著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到日的外國人將現代運動一併帶進日本,軍隊與學校有外籍老師進行教學,學校裡則有運動社團、課後活動與運動會等,加速運動風氣的蔓延。但傳統劍道在現代軍隊裡轉變為精神意志的鍛鍊,相撲因少了將軍、大名(土地領主)的贊助,被認為不文明而一度有要求廢止的聲浪。 至於柔道,有關鍵人物嘉納治五郎的出現,將其技術制度化及理論化更加普及,之後更散播至世界。1909年嘉納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積極將奧運介紹給國人認識,培育許多體育能手,自1920年參加奧運比賽陸續有所斬獲,日本便萌生舉辦奧運的念頭。 在嘉納的運籌帷幄,東京成功申請1940年的奧運主辦城市,卻因1938年中日戰爭被奪回主辦權,後也因二次大戰使得奧運接連停辦2屆。這個遺憾,或許也是為何在1964年成功舉辦奧運時讓日本人特別興奮,因為他們急欲從戰敗國處境回到世界的運動場上揚眉吐氣,拿回民族自信心。 1964年,進入到迄今令人懷念的昭和時代中期,從戰後復甦經濟急速起飛,有所謂的「新三神器」即:彩色電視、窗型冷氣及汽車,用以代表當時的生活,為了奧運則有首都高速道路的通車及東海道新幹線啟用,連結關東與關西的交通網絡,以及首次啟用衛星來直播奧運。 作為日本首都的東京,拿回原美軍駐軍用地的原宿、代代木區。大興土木,由丹下健三設計足以代表上個世紀建築地標的〈代代木國立競技場〉,以混凝土打造薄屋簷、懸吊系統吊掛屋頂,完成當時全球最大張力構造、外觀又如螺貝般有機造形的現代建築,並有象徵民族特色的寺廟屋簷,強勢彰顯設計技術與建造工程。 當時參與奧運的設計師幾乎都成為一代大師。時任藝術總監的勝見勝籌開「設計懇談會」,召集龜倉雄策、濱口隆一與原弘等共同商討視覺規劃,包括Symbol Mark、色調與字體等;延攬年輕設計師:杉浦光平、田中一光等,還有工業設計師、建築師一同參與奧運會場的大小製作物,聖火火炬是柳宗理設計,聖火台設計是岡本太郎,就連紀念徽章都由岡本與田中一光合作完成。 其中在競賽與設施中導入PICTOGRAM圖記號的設計系統,跨越語言藩籬,山下芳郎設計20種「競技SYMBOL」與年輕設計師:福田繁雄、橫尾忠則與榮久庵憲司等,在3個月內完成36款「設施Symbol」,搭配特粗黑體樹立製作的準則,會後放棄著作權並贈與國際奧委會,也讓下屆主辦國墨西哥補足其它競技項目延續至今。 1961年發表第一張官方海報,裡頭的Symbol Mark抓住了大眾的眼光。中間象徵紅太陽的紅圓,下方緊接配置著金色五輪,是全國對初次舉辦奧運的期待。隔年第二張海報,則以各國跑步選手起跑的瞬間照片作為主要視覺,在過去盡以插圖為主的創作來說是一大突破,無論在構圖、光線與層次感等皆展競技之美,彰顯日本各方面技術的成熟與國際水準,迄今仍為經典。 1964那年,聖火還傳到台灣。開幕前發表的最後一張海報,係以照片紀錄了選手在傳遞聖火的情景:黃昏的地平線上,靜謐氣氛中持著柳宗理設計的聖火火炬,莊嚴神聖裡,似乎就要將聖火帶進會場。 歷經半個世紀後,聖火又將再度回到東京,而此次的火炬將帶來什麼?在半個世紀後又代表什麼?留下什麼?在期待2020之餘,更令人擁有無限想像。 聽廣播 |